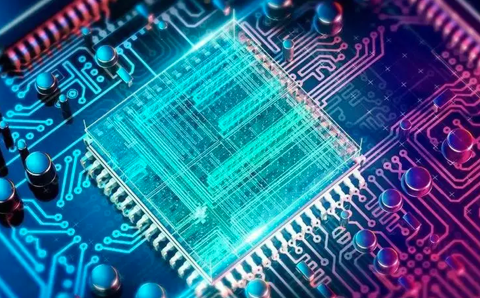纪实,还是审美?
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宋立民 发布时间:2017-05-19
随着剧坛“赵瑞龙丁义珍组队走红毯,《人民的名义》主创聚首超搞笑”的热闹,文坛的沉寂越发鲜明。鲁迅先生曾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是电视剧一播,河南、湖南等地的“丁义珍窗口”瞬间得到了改造,这是“真实”与“地气”的力量。因为重大题材有其必至的力度,“微时代”的文艺再次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融为一体,而“纯文学”的努力很可能仅仅是退回“审美圆心”的继续边缘化。
“华”与“素”
前不久,余秀华“掐”上了范雨素,笔者即刻想到“七步诗”曰“相煎何太急”。二者作为“苦难姐妹”,似乎不必VS。
关于范雨素,余诗人对记者讲了四点:“一,文本不够好,离文学性差得远。二,每个生命自有来处和去处,不能比较。三,每个坚强的女人都很辛苦,不值得羡慕。四,我都不愿意和迪金森比较,何况是她。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知道是真话还是宣传策略,总之,在母亲节前夕,吃了半辈子苦的女诗人侈谈“文学性”是有点幽默的。
说实话,两年前,读了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为代表的余秀华的作品,笔者实在没有感觉到“质朴滚烫、直击人心”的“天才”,更没有初读迪金森的《先生,我为什么爱你》、《暴风雨夜》等诗作的冲击力。虽然见仁见智诗无达诂,但是比较一下余光中的《双人床》:“今夜,即使会山崩或地震/最多跌进你低低的盆地/让旗和铜号在高原上举起/至少有六尺的韵律是我们/至少日出前你完全是我的/仍滑腻,仍柔软,仍可以烫熟/一种纯粹而精细的疯狂”,你会发现,女诗人还是缺少了重要的意象与细节。而且,即便不缺少细节,“睡你”的“双人床”或者行军床也还是无法与《我是范雨素》的厚重相比。读范雨素,笔者回到了五四“问题小说”与新时期“知青文学”的感觉,她写道:“按照知青小说教我的七十二道伎俩,逃票去了海南岛。那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马路上有木瓜树、椰子树。躺在树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我吃水果吃腻了,就上垃圾桶里找吃的。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生活的。”上访时,维稳的年轻人“照顾”她80多岁的母亲而只是拉了一下,胳膊脱臼了——这种叙述方式,让笔者记起了自己推荐给大学生的散文:《谁比谁活得更长》。论美感、论文学性,论细腻的女孩子心态,范雨素与北大才女都不在一个级别上;但是,在那些不紧不慢的陈述面前,文学性已经自觉靠后——诗歌的细节是要提炼的、编织的,范雨素不需要,她除了陈述还是陈述。而且,议论母亲与自己的孩子分开,她说:“凡是养过猫狗的人都知道,猫狗是怎么护崽。同理,人是哺乳动物。抛弃孩子的女人都是捧着滴血的心在活。”——在母亲节读到这样的文字,任何诗歌都会黯然失色。
所以,窃以为《我是范雨素》与《人民的名义》是同一类作品,其共同立足点是人民的生存状态,区别仅仅在于大的政治生态与小的打工生活。
“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不错,问题在于如何记录它,叙述它。不然“独一无二”就是“几乎是真理”的空话。因此,“华”与“素”在此刻并非一个世界,即便她们都明白:靠稿费生活会继续挨饿。
诗与真
当年鲁迅评论“革命诗人”殷夫的《孩儿塔》说:诗集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笔者的感觉是,如今的“微时代”,正在经历着“否定之否定”。要回到简洁、粗砺的现实当中——这是与“走转改”的大背景丝丝入扣的。
上个月,外孙女考南开新闻研究生参加复试,咨询我这“老系主任”应该重点准备什么,我告诉她:阿列克谢耶维奇。复试结束后,她说提到这名字,导师们眼睛亮了。
就新闻调查或曰“报告文学”而言,从瞿秋白的《饿乡记程》、《赤都心史》,夏衍的《包身工》,茅盾主编的《中国一日》,到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何建明的《落泪是金》,虽然文字不无细腻与粗疏之分,但是登上文学史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进入新时期,以反思历史为基调的深度报道,曾经吸引了无数眼球,推动了拨乱反正的时代大潮。因此,写实还是虚构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文字“撄人心”而切入历史的深度与广度。阿列克谢耶维奇以“慢工细活”的“低产量”,记录了俄国革命、二战集中营、苏联阿富汗战争……她坦言:“在采访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成为见证者,是那些闻所未闻的全新故事的唯一倾听者”。换言曰,她书写的主题已经是自己的“炼狱轮回”。她强调:“我写的是人类的感受,以及在事件中他们如何思考、如何理解、如何记忆。他们相信什么,又怀疑什么?他们经历着怎样的错觉、希望亦或恐惧?”——在一个求真务实的时代,文学正在厚重地回归“纪实”的界面。与她的“纪实文献”相比,“伟大的陪跑者”村上小资而时尚的情感绘写,确实有点“小巧玲珑”了。
至于种种“越位获奖”而“捍卫虚构特性”的议论,也同样站不住脚:从设奖至今,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多位得主里,显克微支、比昂松、吉卜林、法朗士、托马斯·曼、奥尼尔、海明威、加缪、肖洛霍夫、川端康成、辛格……都做过记者编辑,马尔克斯当了多家媒体的记者与专栏作家,本来就在“位”上。而没有得奖的斯托夫人,用纪实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酿成一场废奴大战”,其取材正是黑奴乔赛亚·亨森的自传。普利策1917年已经设立了文学奖,诺贝尔向纪实的新闻“倾斜”一回,同样无可厚非。
“诗与真”是歌德晚年的自传,其结尾说:“光阴的白驹像是被不可见的幽灵鞭策那样拽着我们的命运的轻车走了,我们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勇敢的镇定的紧握着马缰,催动车轮,时而左,时而右来闪避这儿的石头,躲开那儿的悬崖吧。”这正是普利策“险滩暗礁论”的注解。大作家兼理论家没有说“审美”。因为面对严酷的现实,“真”就是“美”。这也是笔者认为范雨素能够“活得更长”的理由。
今与昔
针对范雨素VS余秀华,王家新先生评论说:“在这样的事情上我宁愿相信普通读者,普通读者靠的是他们的本能和直觉,好就好,感动就感动,而那些所谓‘专业人士’却在那里打太极,天知道他们在兜什么圈子。”
关于“文本”、“审美”、“文学性”的研究,几十年来,已经汗牛充栋以至于成为旧话。然而,随着文学的日益“边缘化”,理论越来越疑似评论家们评职称拿科研奖的“自拉自唱”。简单地回顾,文学的“如日中天”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候文学站在历史的潮头甚至舞台的中央,无论是正剧还是悲剧,写历史还是关注现实,总在为万众瞩目——文学为当年的拨乱反正摇旗呐喊,功不可没。
然而市场经济的大潮滚过之后,情况大有变化,“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之下,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更加迅速地被‘消解’为各类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其尊卑贵贱,都要通过‘市场’这个大考场上的拼搏竞争而一见分晓”。(雷颐)于是在铺天盖地的周末副刊、网络主页、广告文艺、时尚杂志、卡通漫画甚至“黄段子”面前,“纯文学”日益成为奢侈品和“多余的话”:“90后”不屑一顾,“砍手族”们忙于购物车,而上班族又往往没有了那份欣赏的闲心。当初一呼百应、旋乾转坤的“中流砥柱”逐渐“失位”。实际上,文学“如日中天”而为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时候,恰恰是“审美”、“解构”、“体系”并不时髦的时候,当年轰动一时的作品,现在看来,相当一部分是艺术上比较“粗疏”的。但是,当时的“粗疏”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精神相一致,与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相一致,集中而有力地表现出严格意义上的“诗”的精神的复归:激浊扬清,摧枯拉朽,以独立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摆脱四人帮“阴谋文艺”的桎梏,以“原生的粗砺”彻底告别矫揉造作、千部一腔的陈词滥调。
回观现在的《人民的名义》与《我是范雨素》,大家同样可以找到这样那样“审美的不足”,细节的缺陷,然而,恰恰是充满真情实感的“纪实”,让作品发出黄钟大吕的声音。白居易《与元九书》曰:诗歌是“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有了真情的“根”,才可能谈到修辞与藻饰,而不是因为“审美”的完整而忘记了与时俱进的“根”。
责任编辑:《每日财讯网》编辑
上一篇:“道钉”身后的家国故事
下一篇:莎车好人老杨

〖免责申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其图片及内容版权仅归原所有者所有。如对该内容主张权益请来函或邮件告之,本网将迅速采取措施,否则与之相关的纠纷本网不承担任何责任。



 海运费暴涨、“一舱难求”再...
海运费暴涨、“一舱难求”再... 桥水Q1疯狂扫货美股“六巨...
桥水Q1疯狂扫货美股“六巨... 光伏企业竞相布局 0BB技...
光伏企业竞相布局 0BB技... A股突发减持潮来了!近20...
A股突发减持潮来了!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