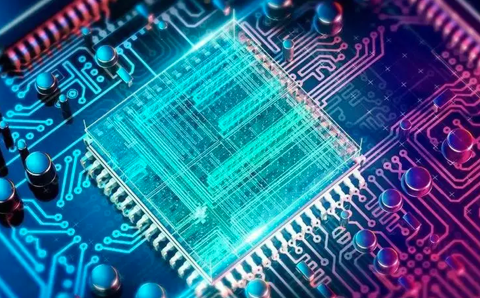《半个父亲在疼》:人间至情的极致表达
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每日财讯网》编辑 发布时间:2019-06-21
父爱如山,一半温暖,一半疼痛,这或许是许多儿女的共同情感体验。
6月16日,父亲节当天,作家庞余亮《半个父亲在疼》分享会在北京SKP举办。诗人、诗歌评论家、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家新,散文家、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周晓枫,与作家庞余亮一起,怀念那个让人心疼又让人温暖的父亲。
《半个父亲在疼》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蕴藏了作家对父亲、母亲以及个人私密成长史的坦诚书写,是一次人间大爱的极致表达。至真的坦白,至疼的亲情,催泪弹般文字,穿透了世间尘埃,让我们看到岁月无声的流逝,亲情的暖心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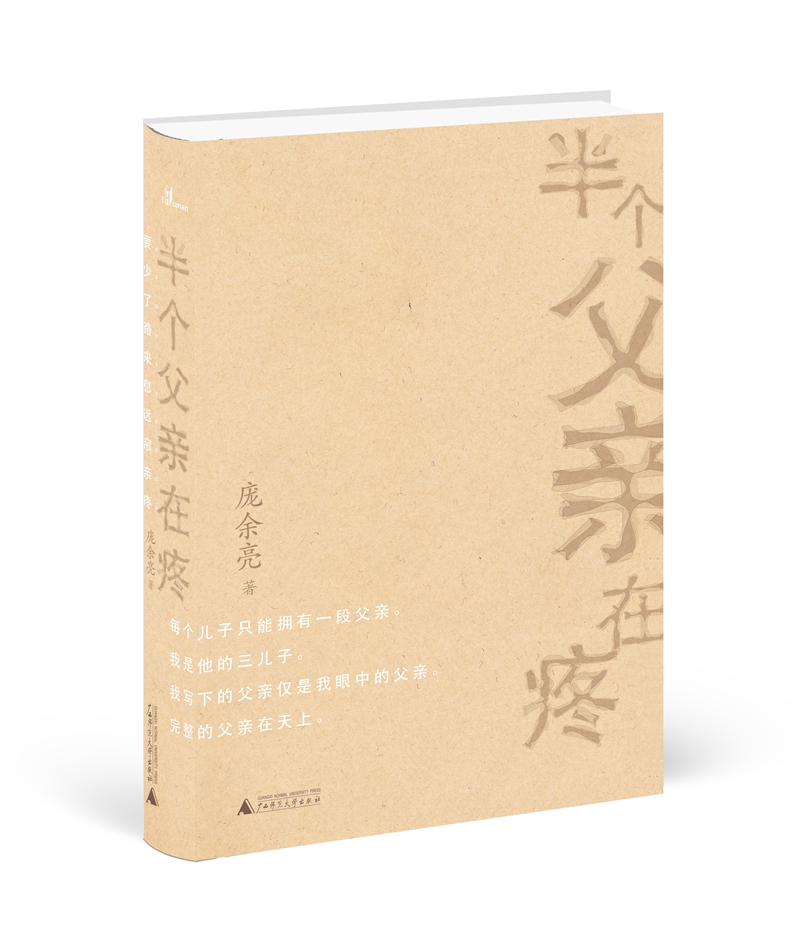
对话实录:这种文字是慢慢酿出来的

贺嘉钰:今天是父亲节,欢迎大家来参加庞余亮老师的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北京分享会,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参加活动的几位老师。著名诗人、评论家、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老师,著名散文家、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周晓枫老师,欢迎两位老师。还有今天的主角,这本书的作者,著名散文家、小说家、诗人庞余亮老师。
我读了这本书有几个关键词不断在我脑袋里,父亲、家庭、消失的乡村,我觉得庞老师一开始就把我们之前在文学里面不常见到的半个父亲的形象搁到了我们面前,这本书又是大于这半个父亲的,他还书写了亲情、亲人之间的关系、父母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等等,所以我觉得庞老师应该是用父亲这样一个形象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记忆怎么抵抗以往的故事。整个一本书就象一首乡村生活的抒情诗或挽歌。王家新老师和周晓枫老师作为作家和专业的读者,请你们先聊一聊读这本书的感受。
王家新:我记得余亮家乡的双黄蛋,余亮是很好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他是双黄,像我们是单黄,单黄很容易下出来。余亮这些年诗集、小说、散文集都不是一般的泛泛之作,都是呕心沥血的凝聚了他的挚爱和疼痛的作品。现在我还没有读完,他每一篇都能抓住你,都让你感动。
周晓枫:余亮这本书里最感动我的还是这篇半个父亲在疼,它牵扯了很多,人类和大自然不一样,大自然很多动物界生物学的父亲像鱼卵一样就消失在茫茫人海,我们会把很多家庭的责任赋予在人类的父亲身上,很多人包括作家一都生在写跟父亲缠斗乃至纠葛,可能有些作家一生都没有摆脱跟母亲的关系,包括我,我至今没有敢触碰这段对我来说比较深入的话题。我觉得人类的情感为什么不一样呢?一只母猫照顾小猫的时候会把最弱的叼走,放弃最弱的,但人类的母亲永远会保护最弱的,人类和父母的关系包括人类一生中难以解除跟父母情感上精神上视野上的关系是特别重要的,它牵扯到我们很多更深入的地方。
我当时看这个书特别感动,我觉得这里有足够的诚恳,有足够的作家的力气,这种文字是慢慢酿出来的,像一个树分泌树脂一样,不是我们修辞学上掌握了技术就能应用的技术。你能看到父母给了我们皮肤和血肉,你会发现我们不断撕扯的过程中最后是血肉斑驳甚至体无完肤的状态,我们小的时候不想成为父母那样的人,我们主动地想撕裂这种关系来获得自己的成长,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过的是没有父亲的父亲节,没有母亲的母亲节,我们的情感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更深入的交缠着过去,我看到这个部分让我非常动容。
记忆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人性的真实
贺嘉钰:晓枫老师说的这段大家听了一定会觉得特别动容,说到余亮老师有足够的诚恳在里面,这本书的第一集就是几篇关于父亲的散文,我们读书的时候会看到关于父亲亲切温情的部分是很少的,大部分写出的是有点暴怒、有点脆弱、有点无助甚至不堪的父亲,我想请余亮老师谈一谈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挣扎?您是用什么样的勇气写出不完美的父亲?
庞余亮:我父亲一直是文盲,做过一个职业—养鸭子。我家从小养鸭子,鸭子是会吃蛇的,我经常看到一个鸭子把蛇吞下去,鸭子的能力很强,我父亲因为家庭比较穷所以脾气特别暴躁,1989年春天我父亲高血压中风在家,我每天为他服务。父亲一辈子都是在村庄里的英雄,他一旦中风之后被困在那个身体当中,他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跟他相处的五年时间里我们俩人没有任何感情,他脾气暴躁就开始骂人用拐杖打人,给他洗澡的时候因为重心不稳跌下来,然后就开始骂,我就跟他对骂。
1994年的秋天我父亲去世,后来我写了一首诗,朋友的父亲2017年秋天去世,我有感触写了父亲总是死在秋天里。1994年去世之后我没有为父亲写一篇文章,因为感情就是那样的感情,我后来跳到靖江电视台,我在小县城的人民公园门口看了一个中风的老人扶着个拐杖,我要扶他走一走,扶着他从公园的门口转了一圈,他身上的气息就是我父亲的气息,中风老人的气息是一样的。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写这篇《半个父亲在疼》,当时是用电脑写的,敲到父亲这个词的时候键盘就卡住了,我以为是我父亲不让我写,因为那是晚上写的,后来才发现是我用力过猛间键盘卡住了。这个散文是一口气写完的,我重新去体会我父亲,我父亲母亲生了十个子女,活下来的是六个人,我是第六个,这样的家庭中他的脾气暴躁不堪都是有可能的。昨天从无锡到北京的火车上我拼命想父亲跟我之间有没有温暖的部分,我讲一讲父亲给我的温暖的细节。
第一个细节,1983年我考上了大学,在扬州上大学,我父亲送我到扬州上大学,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他把我送到学校门口就不进去了然后就走了,他告诉我两个生活秘密,一个人在外面生活有两个细节要记住,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在夜晚来临之前找一找厕所在什么地方,可能在座的不懂,因为过去厕所很少,家里没有卫生间,招待所也没有卫生间,晚上到任何陌生的地方首先要找到厕所,否则夜里找不到人问,这是他的生活经验交给我的。第二个细节,他警告我做一双布鞋很不容易,你要记得经常把布鞋拿到太阳底下晒晒。他有限的生活经验传递给我的就这么多。回过来写这个文章,怎么写父亲过去的故事,既然我读书我写作,我理解父亲,我身上也有我父亲暴戾的影子,只不过是读书改变了我,读书已经把暴戾压得很低。家新老师是我的榜样,周晓枫老师也是我的榜样,读书写作改变了我,写《半个父亲在疼》,大家都说这个文章写得好,反过来通过他的生活通过我的追忆也能重新理解父亲。
周晓枫:我有点感慨,有的题材是一生给你准备的题材,你说的暴躁让我特别触动,为什么老年人变得越来越自私,我的朋友跟我讲妈妈把儿子的钱全部用来买保健品了,很长时间后我们才反映出他是老年痴呆症,我们觉得他很自私怎么不顾儿子的未来就管自己,还有一个误读是老年人体能下降之后无力自保以后严重缺乏安全感,他会觉得全世界都潜在地存在着对我的伤害,这时候他有巨大的委屈,无法释放,不管是因为过去的权力、对社会的支配权对儿女的支配权被剥夺,还是他的身体能量他无法处理自己,虽然不至于无法自理,但是很多时候是他的行动受障碍,他无法抒发这种委屈,他潜意识都未必会梳理一下,他的暴躁包括被生活所改变被岁月推到彼岸对死亡的恐惧种种搅合在一起体现为对亲人,因为他没有别人可以发火,如果不是亲人的话没有人有耐心有兴趣容忍你的暴戾,别人接触一次就不跟你接触了。有时候我爸爸也会有暴躁,原来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我还愿意带他去最好的地方,当我受了委屈之后还学会慢慢的吞咽和消化,重新感受一次不愉快的暴躁。有一天我们也会如此,我们未必有今天的体能去维护自己的理性,也未必有体能去维护自己的尊严,我觉得暴躁有时候有助于体验我们的父亲们。
王家新:父亲的话题,我读了特别感动,因为我们经历很相像,我的父亲也是晚年脑溢血中风,开始半身瘫痪,后来全身瘫痪,我们很多经历非常接近。我没有像你那样接近父亲,我写母亲更多。余亮这个散文尤其写父亲这几篇,我觉得值得我来学习,首先它非常真实,有种肉体的感觉,比如半个父亲在疼痛是身体的感觉、肉体的感觉,这是非常真实的,不是抽象的理念,用你散文中的话一篙抻到了底,肉体的感觉疼痛的感觉很真实。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非常感动,父亲中风以后身体左臂枯瘦,右肩疼痛,你写得很真实。《半个父亲在疼》里面很多很真实很写生的骨肉的肉体的感觉贯穿到写作之中,这点我觉得真是好。他赋予我们的语言有很真实的质地,不空洞、不抽象、不模糊,都是很真切的肉体的感受和经验,他还把精神完全贯穿在其中。另外他一个很真实的地方,他写他父亲,但对生活对生命那种爱恨交加、悲喜交集,写到这种程度非常难得,他绝对不是单一的情绪感受,他一下子搅和在一起。
余亮有种顽童的气息,他是老三,小儿子,我是老大,这不一样,他从这个角度来写父亲和我作为老大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有顽童的东西。中国乡村生存的智慧、幽默感、疼痛的感受完全搅和在一起,悲喜交加,这种感受我很佩服,真的写得不错,写到这种程度是一般作家很难达到的。骨肉的复杂的矛盾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喜交加的全呈现出来了,他很真实的叙述细节,他不是那种刻意修辞的写,他把真实的父亲、自己的生活像穿越瀑布般穿过陈词滥调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文学写作很重要的东西,这个让我很佩服,甚至敢于写他父亲的狐狸精,这个非常精彩,母亲老是骂他父亲是不是又想那个狐狸精了,这个带有喜剧的成分和人性的真实,他作为儿子有勇气直面生活的真实。是虚构吗?
庞余亮:不是虚构,我母亲从小就往我脑袋里灌输,其中亲爱的老韭菜的前因后果就写了这个部分。
王家新:这是非常精彩的一笔,他作为一个儿子完全不忌讳不掩饰这些,记录记忆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人性的真实,他写得非常富有戏剧性,那种真实的力量真是让人心动心颤,虽然用喜剧的笔调写出来,我很佩服,真实的力量很难达到。我讲了我自身的感受,我是老大你是老小,儿子和父亲关系非常古老,不像母亲那样,甚至非常黑暗,说不清道不明。我是从父亲的角度写儿子,我有两个儿子,后来我开玩笑讲两次婚姻两个反叛的儿子,儿子和父亲这种关系这种纠结。正好今天是父亲节,我念一首诗,《和儿子一起喝酒》,我大儿子在美国读研究生,多年不见,我去看他,到酒吧后就有了一首诗。
一个年过50的人还有什么雄心壮志,他的梦想不过是和久别的已长大的儿子坐在一起喝上一杯,两只杯子碰在一起那就是他们拥抱的方式。中国的父子很少拥抱,喝酒两个杯子碰在一起就是他们拥抱的方式,也是他们和解的方式,然后什么也不说,当儿子起身要另一杯,父亲则呆呆地望着杯沿的泡沫流向杯底。正好也是余亮的主题之一,写和父亲的关系,父子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写。我的父亲也是半瘫甚至全瘫,你们都看到了暴躁、委屈,我的父亲经常在空中乱抓,我非常震动,保姆说有一天忽然不抓了忽然安静了,很怪,一下子安静下来了,他们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要记录我们的父亲的事迹不那么容易,靠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比如你自己当了父亲之后,你当父亲了吧,可能更多的理解了父亲。
文学的美不仅包含愉悦温暖,更包含震撼疼痛
贺嘉钰:家新老师写的诗处理父子关系的还是一首我印象也很深,叫《送儿子到美国》,父子关系可以从很多维度打开,有儿子对于父亲,也有父亲对于儿子,这本书是去年8月份出版,我记得新书发布会上余亮老师说过这么一句话,你说这本书前前后后的写作有30年,到这本书出版你终于越过了写父亲母亲的障碍,以后也可能不会再去写关于他们的事情了,我想请您说说您越过的障碍是什么?
庞余亮:我回过头想想我能读书写作还得感谢父亲,我们家弟兄三个,我父亲给我下的命令,考试留级就回家,我大哥上到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二哥没考上初中,回家打了好几次,我知道家里的家训,只要你留级就回家,我不能回家,所以我六岁上学,16岁考上大学,我一口气考上了,回过来还要感谢父亲,我考上大学以后父亲固执认为你文能了武不能,他要让我把他做过的农活全部学一遍,那时候我拿国家的工资,我到假期就跟他闹矛盾,要干农活,他说将来有一天你会吃不上饭养不活自己,他不认为你写作能养活自己,他认为学会农活才能养活自己,这是他的观点。所以我的父亲对农活样样精通,我遗传母亲,我父亲为什么看不上我也有这个原因,我的性格也像母亲,父亲在教育方面是粗暴的教育方式,我跟他之间是爱恨交加,这个书出来以后我想真的得跟他告别了,他在天上很安详,这个写完之后我真的没有再写有关父亲母亲的文章,我写完了,他给了我我也偿还了他。刚才说父亲坐在膝盖上,跟儿子一起喝酒,这些细节我都没有,我跟父亲只有一次有关写作方面的交流,上大学二年级我疯狂地写诗,八十年代是诗歌的王国,每个人都在家里写诗,我也在家里写,我写了一半父亲说你在干什么,我想告诉他我在写诗,但是你要知道我的父亲是文盲,你解释诗歌要解释多长时间,你无法解释,我想了半天跟他说这个东西写好了可以上报纸,上报纸他懂,他说上报纸干什么?我说上报纸可以换钱,这个懂了吧?他说你写这个可以换多少钱?那时候一首诗可以拿8块钱稿费,我说可以拿8块钱,他想8块钱可以换一百斤大米,他说你今天就写,不要干其他事。这是我跟父亲有关文学的交流,他不懂什么叫文学,不懂书本,更不懂什么是诗歌。我父亲去世最大的悲痛在我身上,父亲去世那段时间我没有为他写一个字,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空空的在田野上奔走。那时候看《一句抵一万句》我真的懂,父亲去世那几天我一个人在外面狂奔,不知道说什么,也不能写,心中很悲痛,不停的奔走,这个奔走的情景就在我心里留下了,父亲离去的疼痛转换成了奔跑。
周晓枫:这本书我最喜欢的是《半个父亲在疼》,里面包含着成长中有羞辱甚至对自己不满,你写了干农活,父亲让你撑篙,写得很详细,我们在积累了成长中有锐痛有自痛有不言自明的隐痛,积累下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扶着中风老人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一样,你的一切经验复苏了再去写这个,席卷的力量之下来不及修辞,有时候太锋利的东西挂不住修辞,太强烈的感情会席卷着裹胁着你的表达去走,通过这个我会看出余亮是饱含诗意的人,他写母亲,我第一次知道植物是吃头发的,他跟孩子相处,他对生活的发现,他是在生活中非常向往诗意保存诗意,他在写作中对诗意的把握有不稳定的时候,有些修辞上,这个过程是很必然的,我看自己的作品,我会觉得以前怎么会写得这么傻,为什么一个漂亮的修辞安在门牙上,那么老远就亮出来,生怕别人看不见,我们生怕别人看不见我们别致的处理、对生活独特的发现,机遇把文学上加工化的诗意交给大家的时候都会留下写作的痕迹,慢慢的记忆成熟以后甚至荷尔蒙降低以后就不会那么夸张嚣张地强调你的比喻。虽然父亲没有受过教育,明显《半个父亲在疼》是更真挚更强烈更触痛更有个人的感情能量负载,我觉得这种文字永远是更打动人的,虽然他是文盲跟你没有交流,我自己有个毛病,我们沉浸在诗情、比喻里、视觉上的摆换得意里,并不是很好的带动写作者向前运行的方式,父亲没有在文学上跟你具体交流,他跟你的交往和你后来形成的经验的认识是你把自己运抵了更远的地方。
王家新:我们过去说庞余亮首先是个诗人,他的诗都是抒情、文学的词藻、优美等等,但我觉得这本书打破了这些东西,他没有把生活的美化诗意化,他没有这样做甚至拒绝这样做,最后我们感觉这还是诗人写的文字,一般人没有经过诗歌训练是写不出来的,他打破了我们对诗的理解。通过诗的技巧可以看出来他不是刻意显摆,你看不出来他心里有,比如半个父亲在疼痛,中风这种身体的感受,结尾特别好,他无限扩大了,看到其他中风的老人拄着拐杖艰难的行走,那是他的半个父亲,这是扩展的。这是诗的手法,他不是表面的写文字。
庞余亮:豆瓣上有一个作者不知道是谁品这本书,他的标题很长,标题叫《一个恋父男人的标准样本》,像我这样反复书写父亲的是恋父,但是他有一点是对的,我渴望中的父亲和我现实中的父亲并不是吻合的,因为我渴望很完整很标准很慈祥的父亲,但生活给你的就是这个父亲,你必须要写他,他给我们的生活太怪了,给我这样一个父亲给我这样一个母亲,我要理解他,我觉得理解透了所以我不再写了。
周晓枫:换句话说,讲文人趣味的时候特别容易沉湎于修辞搭配的美,我觉得真正的文学上的美不仅包含了让我们愉悦让我们温暖,也可能让我们震撼让我们疼痛,生活和我们经历的东西拓展了我们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
爱不能相等,才使爱的人更想爱
贺嘉钰:谢谢几位老师,我听了特别感动。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两位已经做了父亲的老师,你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书写过父子的关系,你们也做了父亲,你们觉得自己做了父亲之后对父亲的理解有变化吗?
庞余亮:我结婚生孩子就是为了父亲,这个细节我没写,写的话怕我爱人生气。我做了父亲后,尽量去掉父亲最大的缺点暴躁。父亲勤劳,是我们村庄起床最早的人,每天早上5点钟把我们全家人全部叫起来干活,5点钟天还没有亮,我的姐姐负责干什么我妈妈负责干什么,全部忙完了别人才醒过来,这是我父亲的优点,父亲留给我的还是很多的,只不过他的生活,因为他的成长环境跟我太遥远了,顺便说一句今年是我父亲整整100岁,他和汪曾祺同岁,我为了追求我父亲的痕迹,我把汪曾祺全部研究了一遍,研究汪曾祺就是研究我父亲当年的成长轨迹,有一部分只能靠想象。
王家新:我对父母的观察感受是做父母就是爱、忍受和牺牲,这是他们给我留下最重要的东西。不说早年,我父亲晚年瘫痪,这对我是一个振动,他行走非常困难,我们开车回湖北老家,快要走的时候父亲突然出现在门口,不知道他怎么走到门口,提了两瓶五粮液一甩一甩让我带回北京,我真的很振动,这是爱的力量产生的奇迹。他行走非常困难,他走到了很远的门口。它不是一瓶酒,是父母对我的爱,从父母身上一直感到爱、奉献和牺牲。
我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但我是一个尽心的父亲。我老二上人大附中,个性很强,拒绝跟我一起出门,他可以在家里点餐,不愿意跟父母一起出去,我完全理解他。我翻译的诗中有一句,如果爱不能相等,让我成为爱的更多的一个,当然讲的是情侣之间,这句话被很多人喜爱,父亲和孩子之间爱就是天赋的东西,无论他给你带来什么你都必须去爱,这是天命,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你也不能要求回报,我对孩子尽了我的爱,无论能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我不去想,我必须如此,我必须这样去做,无论代价是什么回报是什么。
我当了父母的这种经验,唯一的徒劳感,放在一般的父亲子女可能不太合适,因为我们是搞文学的人,有一个问题,就像卡夫卡的一首诗写的,卡夫卡终生未婚,两次解除婚约,卡夫卡也没有后人,卡夫卡的痛苦无人能够继承。如果有点痛苦或某种徒劳之感,年轻人能否理解我们这代人,我们的后代下一代能否理解我们,可能是下一代看来很可笑很荒谬的,现在年轻人就是这种风气,他们在一块从来不会赞美父母,你看不到年轻人的微信,他们会屏蔽你,以后可能会改变,忧虑是后来的人们能否理解我们这代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包括了这样一种感受。
周晓枫:一个父亲的离开对别人的生活没有改变,但父亲的离开改变了你的未来,不管是婚姻还是孩子,在别人那无足轻重的力量能把你推到命运另外的轨道上,这是他能够表达的最后的不放心和他不擅长的爱的表达。
王家新:我还没完全读完,不知道余亮是否感到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的父母奉献了一生爱了一生,绝大部分家庭父母都是爱孩子的,舍弃一切爱孩子,为了孩子,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问题在这,他们一生是否有所安慰,我可以从终极意义上讲,我对自己的父母无所安慰,我们家兄妹五个,父母对各方面比较满意,我和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应该说他们比较满足,后来把孩子都抛到一边了,我父亲后来不想我们,他一直哭闹着要去医院,我父亲个儿大,一个保姆都照顾不了,需要两个孩子才架得动,他爬也要爬到医院去,要和我母亲待在一块,我母亲先过世,父亲本来好好的半年之后突然就走了,我们都说他去找母亲了或者母亲把他唤了过去。我母亲将近88,应该说长寿,忍受了十多年病痛,后来我的母亲过世,我写了一首长诗《安魂曲》给我的母亲,像中国芸芸众生一样死无安慰,看着各方面很好,但是从根本上缺乏这个安慰,我不展开更多的细节,我真是感到了这一点。这给我们提出一个终极性的问题,人的安慰何在?
庞余亮: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的开头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一个外国诗人写的,我一直留在脑海当中,父亲是最孤独的,因为他们总是先死,这句话我一直记在我的笔记本上,因为他们承担得太多了,劳力最多,精神意义上也是这样。我有时候都不愿意翻这个书,印出来之后我也不愿意翻,读者告诉我看了觉得怎么样,我很敷衍地跟人家交流,因为交流得越多想得越多。刚才晓枫老师说你放不下,我真的不想再写下去了,因为这个话题已经完成了,我要继续向前走,带着他们走的话可能负担更重。所以我有意识的开始儿童文学创作,我不再接触这个题材。
周晓枫:你有没有想过重新回到儿童文学创作也是对不在的父母的呵护,幻想自己是个孩子,我原来想男女之间爱能维持长久是内在平等,爱在一定阶段不平等才使爱的人更想爱,说起来有点绕,有一种不平等的爱能维持特别长,比如母亲不是贸易不是经济,不计成本不计回报,它甚至谈不上那么伟大,它是情不自禁,它是无法停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使我现在发生变化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我基本没有触及。你从事儿童文学,表面上看你可以保护别人了,内心有儿童的部分,那个小孩没有真正长大,或者由于停止发育或者由于别的,它还呵护着不再存在的父母,我觉得也有可能。
责任编辑:《每日财讯网》编辑
上一篇:用之可以尊中国
下一篇:没有了!

〖免责申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其图片及内容版权仅归原所有者所有。如对该内容主张权益请来函或邮件告之,本网将迅速采取措施,否则与之相关的纠纷本网不承担任何责任。



 海运费暴涨、“一舱难求”再...
海运费暴涨、“一舱难求”再... 桥水Q1疯狂扫货美股“六巨...
桥水Q1疯狂扫货美股“六巨... 光伏企业竞相布局 0BB技...
光伏企业竞相布局 0BB技... A股突发减持潮来了!近20...
A股突发减持潮来了!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