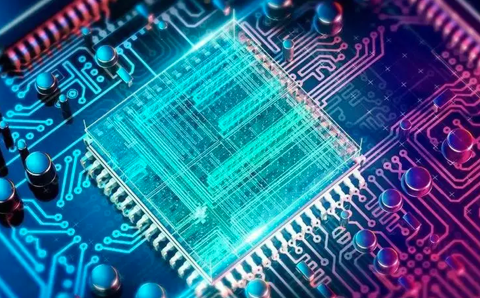一支腐竹载乡愁
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每日财讯网》编辑 发布时间:2019-10-14
独在异乡为异客。周末因临时公务无法回家,一早起来饥肠辘辘,又要赶时间出门,决定自己动手。打开冰箱,发现没有多少存货:鸡蛋,面条。再找,眼前一亮:新桥腐竹!来不及多想,立马生火煎蛋,爆腐竹,下面条,不一会,一碗早餐妥妥当当。坐在餐桌上,我一口热汤,一口腐竹,一箸面条,一种特有滋味通过舌尖,涌动全身,让异乡早晨一下子温暖起来。再深呼吸一口,满屋豆香,心里泛起淡淡乡愁,我的眼睛湿润了。
乡音难改,乡味依然。
腐竹是我从小到大的至爱,有人问我新桥腐竹的前世今生,我一时无法考证,但记得老家盛产黄豆,向来就有加工黄豆的传统。房前屋后、低丘缓坡、田埂都种植黄豆,为腐竹提供了优质原材料。当时人多地少,生产队的田埂大家抢着种,只能按人口划分到户,而且种植还要利用中午或者傍晚收工时间。种黄豆是件累活细活,在田埂上种黄豆要先挖个小穴,然后放入种子,撒上一把尿泡过的草木灰,再把土回填。
我小时候帮母亲种黄豆,每当准确地放进种子、撒上灰,母亲就夸我我一句。每种完一段田埂,母亲捶捶背,总是鼓励我,再坚持坚持,种好下一段就可以回家吃午饭了。为了能够多种几穴豆子,母亲还要计算着把穴挖到田埂交界处的最里端。
当然最累的活其实在后头,即收成期。黄豆种下后,发芽出土长苗,浇水施肥除草,待枝干叶黄,豆角鼓实,就连根收起,去叶成把,再用竹竿一把把串起来晾晒,待豆枝豆壳彻底干枯后去壳取豆。具体工序是拿一把木制锤子,一手抓豆枝,一手锤打豆壳,敲出豆子,最后把豆枝豆壳与豆子分离。整个过程,豆尘飞扬,虽然可以做一些防护措施,但半天下来,手上身上脸上还是沾上不少毛茸茸的豆尘,如果不及时清洗,几天都浑身难受,这些活母亲总是不让我们插手的。
家乡土生土长的黄豆粒小精实,加上独有水土,加工出来的豆腐和腐竹,风味独特而远近闻名,成为家乡待客的必备菜肴。
我对腐竹的记忆从懂事时开始。每逢过年过节,家家户户做豆腐。基本工序是先把黄豆去壳浸泡,用石磨磨浆,然后加水煮开,待温度降到适度,再添加石膏或卤水,最后倒入框格去水成型。每当豆浆开锅,满屋浓郁的豆香味,增添了节日喜庆气氛。豆浆在降温过程中,表面会形成一块皮状的凝结物,用竹签挑起来晾干,色泽金黄,油光发亮,清脆可口,这就是腐竹,有的地方叫枝竹、豆腐皮等。
记得那个年代物质紧张,豆腐保质期又很短,走亲访友难以携带,一些条件稍好的家庭就同时做些腐竹储存起来。小时候嘴馋,父母亲对我这个长子有点偏心,家里每一次做豆腐,母亲用筷子或者竹签挑起来的那层皮,就直接变成我的口中美味,也是我舌尖上抹不去的记忆。
秋风起,做腐竹。上等的腐竹需要好天气,秋冬季节,是加工旺季。一些有生意头脑的人就利用这个季节,收购黄豆加工腐竹出售。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桥腐竹走出大山,摆上了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餐桌。我在广州上学时,每每假期结束,随身带一小袋油炸腐竹返校,参加室友特产会,备受欢迎。参加工作之后,腐竹更是成了我与亲朋好友礼尚往来的固定手信。随着市场需求增加,有人瞄准商机,从外地进豆子,建腐竹加工厂,由手工作坊演变到机械化生产,但风味远不如前。更痛心的是,有个别利欲熏心之人,为了提高产量,违规加入添加剂,严重影响了质量和消费者权益,新桥腐竹名声由此大受伤害,市场逐渐萎缩,种黄豆的人家也越来越少。后来,母亲去世,弟弟妹妹外迁,偶尔回老家,昔日成片的黄豆种植地不见了踪影,闻不到那特有的地道豆香,内心满满惆怅,腐竹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可是,舌尖上总有抹不去的乡愁。直到几年前,弟弟结束了在外打工的漂泊生活,回到家乡创业,建起了腐竹加工作坊,遵从传统工艺和自然法则,只在秋冬季节生产。虽然产量低,价格高,但让许多与我一样的粉丝,又找回了舌尖上的记忆,产品供不应求。
又是一年秋风初起。弟弟从家乡捎来了新鲜出炉的腐竹,我迫不及待打开密封袋子,一股特有豆香扑面而来,一支支闪烁着黄澄油光的腐竹,让身居他乡的我倍感亲切。这豆香才下舌尖,又上心间。仿佛让我看到了在铁锅前熬夜的身影,荒废的土地又重新种上了黄豆……
责任编辑:《每日财讯网》编辑
上一篇:凤凰展翅于京畿
下一篇:满江红·祖国颂

〖免责申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其图片及内容版权仅归原所有者所有。如对该内容主张权益请来函或邮件告之,本网将迅速采取措施,否则与之相关的纠纷本网不承担任何责任。



 海运费暴涨、“一舱难求”再...
海运费暴涨、“一舱难求”再... 桥水Q1疯狂扫货美股“六巨...
桥水Q1疯狂扫货美股“六巨... 光伏企业竞相布局 0BB技...
光伏企业竞相布局 0BB技... A股突发减持潮来了!近20...
A股突发减持潮来了!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