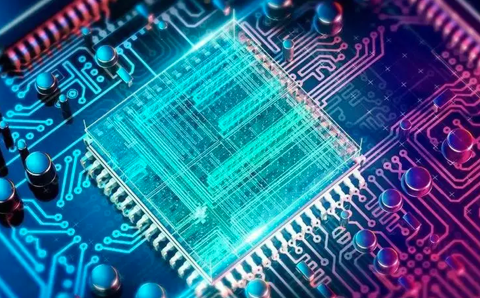除却武昌不是鱼
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宋立民 发布时间:2017-04-14
3月5日,惊蛰。临近天亮,梦见武昌,东湖,依稀有一位老人的声音:“老朋友,武昌鱼还给你留着呢!”
翻身起床,强压着心跳,网搜“樊凡”的名字。满屏是一个歌手的图片。赶紧前置“武汉大学”几个字,遂看到最怕看到的“讣闻”二字。是武汉大学网站——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新闻传播学家、教育家樊凡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2月16日15时24分(美国时间2月15日23时24分)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享年84岁。
樊凡先生1933年9月出生,广西横县人。1948年参军,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5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随后留校任教……遵照樊凡先生身前遗愿,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谨此讣闻。
我明白了:是樊凡先生托梦,告诉我他走了,他准备的武昌鱼我没有去吃,他记挂着自己站过的湛江师院的讲台。
笔者认识先生正好十五个年头。2003年,春节刚过,只身南下的我在经历南下的第一个“回南天”:潮湿到黑板上全在流水,写不上字。室内被褥也是潮乎乎的,我有点郁闷。
学生告诉我,因为刚刚组建的新闻专业缺老师,特聘武大樊凡先生来讲新闻学概论,我便前往旁听——樊凡先生的新闻业务、比较新闻学研究久负盛名,其大著《拓展新闻写作研究的思维空间》、《中西新闻比较论》、《经济新闻范文评析》等,一直是研究生的必读书——听先生讲课是排解郁闷的好办法。
一听课,先生切入的高度和深度,思路的清晰,材料使用的言简意赅,都让刚刚从报社回归讲台的我由衷敬佩。那是我第一次结识这位慈祥的老教授。
课后聊天,更发现这位老者思想一点也不保守,看问题很尖锐又很客观,于是很快成了忘年交。不久我父母来湛江小住,几次与樊凡先生一起吃饭。先生与我母亲同龄,却称呼我“老朋友”。因为我十几岁参军,就在武昌彭刘杨路的部队院里打球,对武昌不陌生。
因为住得近,又都是一个人,我们每周都要聊两次,一般是我准备两个菜、两杯酒,边吃边聊。聊天内容正经的如新闻系的课程设置——“采写编评,吃饭的课,不能丢”,他屡次强调——八卦的如当初武汉美女从窗户上爬公交的麻利,云天雾地。记得他说他主持武大新闻系之际,开了不少文学课、文化课,颇遭议论:“当时也有批评的声音,说我把新闻系办成了第二中文系,本报讯三百字,不要学那么多的文史哲。我是一意孤行地坚持。老朋友,你在《大河报》这两年做深度报道的体会,说明了我的坚持是有道理的。”
后来,樊凡先生主持开会,定下了我们新闻系的主要课程、重点期刊与发展前景。2003年暑假,他把01、02两个年级的同学列表分类,告诉我谁适合做记者、谁适合做编辑,谁可以读研继续深造。2004年春节,他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写来亲笔信,告诉我02新闻班有几位同学身体单薄,因为吃不饱肚子,让我这个系主任想办法帮助,并且特别嘱咐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不要伤了他们的自尊。
每年从美国回来听到我的电话留言,他都会打电话过来。2011年年底,他打电话来,声如洪钟,依旧爽朗得像个孩子。不出三句话就说大学的现状、国家的前景。“经济前进,道德滑坡!”先生忧心不已:“在利益与道德的角斗中,一些人选择了利益,从院士到教授,有的是例子。”先生说,有些单位的领导在一地做官几年,群众的评价不是为老百姓干了几件事,而是三个字:“捞饱了!”“这样的官员能够赢得身后一句怀念的话吗?”樊先生说:“什么都要公关、都要策划、都要运作、社会有时候在畸形发展。”“欧美也有自己的问题”,先生说:“我年年在那里,看的比较清楚。他们自己的体制、制度,也是越来越僵化。为什么危机那么厉害?太自由了!资本的特点是追逐利润,免不掉的。两党之争,原本是利益牵制,有好处,结果是要党不要民众。当年的福利、慈善,如今成了勤快人养活懒汉。有些人就是靠养老金生活。”
樊先生叮咛:“还是那句话,小宋,评论要写,那是本行。你得听我的,写长篇小说,就写大学教授的生活,真实的生活。现在的作品,教授一出来,多半是糟糕的负面形象。事实不是这样,你能写出来!”
那次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恋恋不舍。
几年间,每次与樊凡先生通完电话,我都有立即飞到武汉去看望先生的冲动。他总是说:“我明年还回来,见面的日子会有的,武昌鱼还是要给你留着的!”
我与先生常常说起七七、七八级。我至今仍然觉得有一种力量支撑我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日子、黄金岁月。那时比较穷,却活得真实、向上、纯净。那时候,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激动年轻的心的时代,是樊凡先生那一代人站讲台传道、授业的时代。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的“项目”、“验收”、“评估”、“检查”、“统计”、“评奖”……但那个时候,我们有最大的热情、最多的时间读书、做事。
我告诉樊先生,担忧的同时仍然要保重,该喝茶喝茶、该吃鱼吃鱼,等我去看望他。
记得他离开湛江师院的时候,我还写了一幅字,送到他居住的小楼。
我们都说湛江距离武汉不远,随时能够见面,不料先生再也没有回到湛江。
我把樊凡先生去世的消息发到了2001/2002级同学的微信上。大家发来了悼念的文字、先生的照片和手迹,看得笔者鼻子发酸。一位同学说,樊凡老师上课时,为方便大家,上课用的范文资料都是复制好给大家的,像发试卷一样,最后我们都订成的是一本小册子。有次讲课讲到他在牛棚的事,想往下讲就哽住了,有十几秒。他有句话我们记得最清楚:有时真话不能说,但至少不要说假话。
樊凡先生的弟子、著名的新闻学者、武大博士生导师单波教授说:“晚年的樊老师跃入人生自由之境,光风霁月,超越洒脱,与师母白头偕老,相依相守,云游四方,其乐融融。身边常有学子相伴,谈天说地,诉说衷肠,沐浴在珞珈山的阳光里……”呜呼!都说“新闻无学”,樊凡先生以数十年的生命告诉我们,新闻才是扎扎实实的“人学”,做人不及格,是不可能以讴歌光明、“发现暗礁”、“揭示真相”为己任的。曾经沧海方识水,除却武昌不是鱼。下载了能够网搜的先生的照片,看着先生慈祥而睿智的目光,一遍遍地看。泪流如注。
樊凡先生的新闻业务、比较新闻学研究久负盛名,其大著《拓展新闻写作研究的思维空间》、《中西新闻比较论》、《经济新闻范文评析》等,一直是研究生必读书。樊凡先生告诉我们,新闻是扎扎实实的“人学”,做人不及格,是不可能以讴歌光明、“发现暗礁”、“揭示真相”为己任的。
责任编辑:《每日财讯网》编辑
上一篇:陕西省现代刻字研究会成立
下一篇:“勤奋”的懒汉

〖免责申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其图片及内容版权仅归原所有者所有。如对该内容主张权益请来函或邮件告之,本网将迅速采取措施,否则与之相关的纠纷本网不承担任何责任。



 海运费暴涨、“一舱难求”再...
海运费暴涨、“一舱难求”再... 桥水Q1疯狂扫货美股“六巨...
桥水Q1疯狂扫货美股“六巨... 光伏企业竞相布局 0BB技...
光伏企业竞相布局 0BB技... A股突发减持潮来了!近20...
A股突发减持潮来了!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