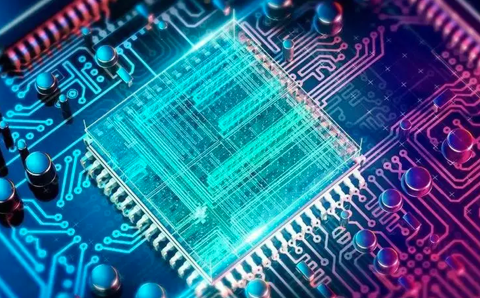庄子的死亡观
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司马朔 发布时间:2017-04-24
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 先进》)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司马迁:《报任安书》)
对任何敏感的思想家来说,死亡,特别是人的死亡,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大问题。人类理性意识觉醒的一个令人遗憾的副产品,也许就是发现:人类可能是这个地球上唯一在死亡之前就意识到自己必死的动物,这为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其精神产品涂上一层抹不掉的忧伤底色。对死亡问题的意识、反思与应对,也许是人类一切精神生活的起点,它的核心任务之一,一切宗教服务于此,并受惠于此。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如果说孔子有意识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庄子则毫不客气地又将它端到桌面上。
庄子快要死了。弟子想厚葬庄子。庄子说:“我把天地视为我的棺与椁,把日月看作为我陪葬的双璧,将星辰当作为我陪葬的珠宝,当世间万物理解为我的殉葬品。为我陪葬的东西还不够完备,还能比这更丰富的陪葬吗?”弟子说:“我怕天上的乌鸦、老鹰吃了你呀!”庄子回答:“露天会被天上的乌鸦、老鹰吃掉,埋在土里也会被蝼蚁给吃掉。从乌鸦、老鹰嘴里抢来又送给蝼蚁,何以如此偏心?”(《列御寇》)
丧礼(即“凶礼”)乃儒家礼仪中的重大节目,这一节目中包括了诸如依血缘亲疏关系如何穿丧服、如何哭丧、如何发丧等一套细密、专业的知识与规范,谁违反了它,就可能被指责为不孝,在社会舆论中就会处于不利位置。庄子对自己未来尸体安排的意见,在儒家乃至今人看来,可谓惊世骇俗,甚至大不近人情。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神仙家思想盛行,上层社会悉心处理自己的遗体以便能让自己的灵魂升入天堂,重享人间诸乐。然而,哲学家均当是理性主义者,用理性的眼光(今天的说法叫“科学的角度”)彻底地推想人类遗体的最终结果,也只能大致如庄子所言。庄子又是个道家思想家,道家的核心理念乃是“道法自然”,即依天地之本然。这种天地之本然用当代生态学语言解说便是:天地间有一条自相循环的能量之流,或是食物链。万物相食,也只有允许相食,天地间的能量才能流动,方可循环。人类自惜其遗体便是人为阻断了这种能量之流,依道家观念这是不应当的;准科学之分析这也是徒劳的。一旦死亡,人类的遗体与万物之遗体一样,无论人类使尽千般聪明,万种能耐,最终的结果还是《圣经》上那句话:“你源于黄土,必归于黄土。”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施前往凭吊。只见庄子正蹲坐着,敲着盆子唱歌。惠施说:“尊夫人与你相处一世,为你养育孩子,然后衰老、死亡。你不哭也就算了,现在却又敲着盆子唱歌,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说:“非也。老妻刚死时,我怎能没有感慨!可细想一下:她一开始本来就没有生命。不光没有生命,本来也没有形体。不光没有形体,也本来没有气。混沌之间,她一变而有了气,气变而有了形体,形变而有了生命。现在她又变而死去。她现在是与春秋冬夏四时节律为一体了。她现在正安息于天地间之巨室,我却在此嚎啕大哭,自以为是未通能达生命之理,所以才不哭。”(《至乐》)
这便是哲学家对待死亡的通达态度,这便是道家对待死亡纯真的自然主义态度。一方面,庄子并没有把人类从万物中特别是检择出来,以为其死亡需要一种特殊的对待——比如,天下万物之死都是稀松平常的,唯有人类的死亡者是最为不幸,因而需要嚎啕大哭,呼天咒地;另一方面,庄子也没有把死亡从天地间生命之流中特别地摘出来,将它当作一件特别不同寻常的事,特别需要人类刻意回避、诅咒的事,而是将人的生、老、病、死理解为天地间春冬夏之四时节律——平常而又相依。正常人类于四季中不能只喜一季,拒绝它季一样;人类也不能于生、老、病、死的生命节律中只选择生之一端而拒绝其它环节。生命现象、生物学规律是一个由各环节构成的完整过程。少了任何一环,世界便不完善,生命不再能循环。生死相随,并不是上帝对人类的薄待与特殊诅咒,而是行之于天地间万物的普遍法则、共享性规律。面对这一铁的事实与规定,又可用庄子一语以述之:“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不是唯有人必有一死,而是天下万物均必有一死,就像是它们均曾有一生那样。在此方面,正可谓众生平等,此乃天地之至公。
生是死之伴,死乃生之端,谁知其中之理!人之出生乃气之聚积。气聚则为生,气散则为死。若死生相伴,我又有何忧虑!所以万物为一体。人们将自己所喜者称为神奇,将自己所恶者称为腐臭。可是腐臭者能化为神奇之物,神奇者亦可变为腐臭之物。所以说“整个天下就是通于一气罢了”,所以圣人珍惜万物之所一。(《知北游》)
只要不把死亡从生命过程中特别地摘出来,将自己的生命从他人的,比如后代的生命中摘出来,将人类的生命从天下万物、地球生态圈的生命洪流中特别地摘出来,每个人都能意识到:每个个体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虚无或不存在,而是换另一种方式,包括其遗体为鸟、蚁所食,或最终腐败、解体分化为无机物,又加入到生生不息的宇宙大化洪流中,又一次加入地球生态圈的能量循环之中。庄子所言的“气之聚散”实在是对当代生态学法则(能量循环)的质朴概括。也只有从地球生态圈的整体眼光,而不是个体人类,乃至人类物种的角度理解死亡,面对死亡这一铁律,个体才不会恐惧,人类才不会孤寂。人类的理性才会真正地成熟,面对死亡,即使没有天国的安慰,每个人的心灵仍可安静如眠,平静似水。这,便是庄子作为道家思想家所达到的境界。某种意义上说,死亡问题实在是测量思想家智慧深度、普通人心理成熟程度的试金石。深刻而不偏执,真挚而能坦然,这便是庄子精神,道家自然主义面对死亡问题之真情味。
庄子对死亡的这种自然主义态度——达观,其实亦可在后世杰出儒者中找到知音,比如宋代哲学家张载即有言;“从,吾顺事;殁,吾宁也。”用今天的话说便是:“老天爷若还让我活,我就好好活着;他老人家若命我立即走人,我也可安然受死。”作为一种生物,惧死当是人最顽固、强烈的自然本能之一;连死这件事都能看得这么开,都可随遇而安,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人百般执著、割舍不下呢?在此意义上,庄子死亡观极近于佛。也许正因如此,历史上喜庄子者只是追摹其轻松自肆的逍遥游审美情趣而已,于生死大关节上并不能如庄子这样达观,此可以我们这个民族恒久的厚葬传统为证。
责任编辑:《每日财讯网》编辑
上一篇:“清明快乐”与“端午安康”
下一篇:“不莱梅的音乐家”纪念银币发行

〖免责申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其图片及内容版权仅归原所有者所有。如对该内容主张权益请来函或邮件告之,本网将迅速采取措施,否则与之相关的纠纷本网不承担任何责任。



 海运费暴涨、“一舱难求”再...
海运费暴涨、“一舱难求”再... 桥水Q1疯狂扫货美股“六巨...
桥水Q1疯狂扫货美股“六巨... 光伏企业竞相布局 0BB技...
光伏企业竞相布局 0BB技... A股突发减持潮来了!近20...
A股突发减持潮来了!近20...